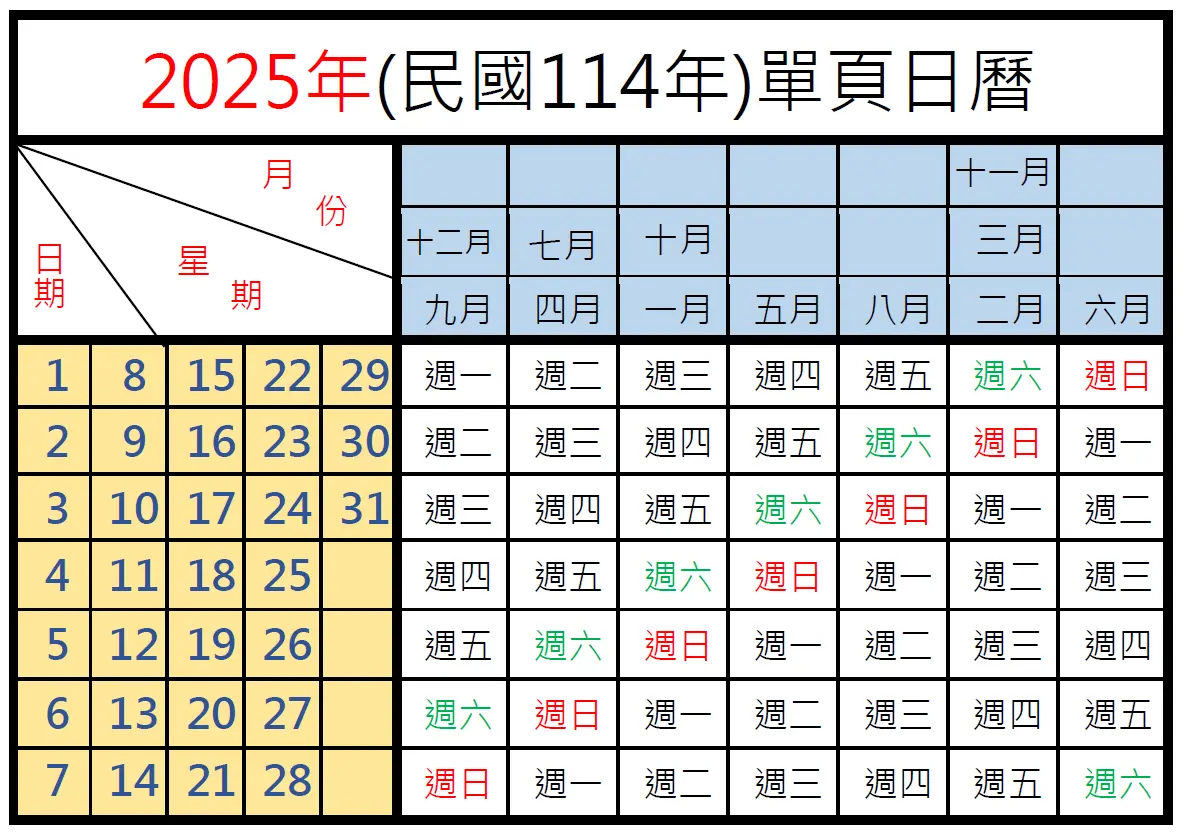慕迪(Moody)說,他第一次主持喪禮時,想從耶穌的教訓中找出喪禮的正確方式及內容。查考之後發現,耶穌根本沒有這方面的教訓,「祂只參加過一個喪禮,然後把喪禮解散了。」這是指拉撒路的復活。
慕迪的話給我快樂的共鳴及痛苦的孤掌難鳴。遺憾的是,共鳴往往來自不信者,難鳴之痛則出自信徒。
曾經寫過一篇文章,裡面強調「死不足畏,生不足羨」。保羅甚至說「死了有益」、「離世與基督同在,好得無比」(腓一21、23)。而活人若不知戒之在色、在鬥、在得;或是長期臥病,造成自己和別人的重擔,那速死還好過歹活。我也批評基督徒和世人一樣,貪生怕死;和異教徒一樣,把永生當作一種肉欲享受的延長。結果,文章退回,主事者(德高年劭的老牧師)說:「不要講這麼多『死』,尤其不要講死有時比生好;要多講點福祿壽財喜的話。」我不覺得這位老牧師是少數。功名利祿的世界心,充斥著許多基督徒。我們不能任他們引人往錯謬裡直奔(猶10-11)。
倒是有些不信主的販夫走卒,也許因為書讀得少,不懂什麼「復興中華文化」或「神學本色化」。當我傳福音時,他們雖然不接受,但會老實肯定一個叫他們極其羨慕的作法,就是基督教的喪禮十分乾淨,簡單,不用花大錢。華人最費時、費力和費錢的典禮就是喪禮。錢穆先生欣然承認,婚喪喜慶中,儒家最重視喪禮。宰我、曹操不想守喪禮,被孔子及後世儒家責備不仁。今天非信徒為死人作法、作七、請風水地理師、花車樂隊、鞭炮鑼鼓,不把活人累死,交通堵死,生態整死(大墓園)不安心。當然,比起埃及金字塔,印度活人陪葬,華人「不問蒼生問鬼神(死人)」的作風,還是小巫見大巫(兵馬俑也不小)。不過,基督教薄葬安民的作風,居然被開明前進的教會人士說「不孝」,應該恢復祭祖;真是開倒車。
我不知道其他宗教民族風俗,但以人性推之,基督教之外任何文明,恐怕都和埃及、中國及印度類似,是把喪禮看得極其重要的。因為他們一沒有赦罪的平安,二沒有復活的盼望,脆弱的心靈只好任由神棍、迷信欺騙擺佈,以燒燒紙錢、紙房(台灣現有用真的,華僑早已有)等宗教儀式來換取虛假的安慰。
活人的信仰
不僅非信徒如此,神的兒女缺少信心時,喪禮也會繁複起來。以色列人到了埃及,學會異教風俗。埃及人為雅各薰屍四十天、哭七十天(創五十3),摩西、亞倫死在曠野時,以色列人舊習未脫,哭了三十天(民二十 29 ,申三十四8)。不過隨著漸進啟示,對真理更明白,復活盼望更清楚,以色列人就愈來愈薄葬。
舊約幾乎不談喪禮。即使談,也是為活人健康而非死人福利(民十九1l以下)。君王死了,一句「葬在墳裡」(如王下二十一26)、或「與列祖同睡」(王上二10)便了。沒什麼「國葬」、「奉厝」等勞民傷財的大典。更沒有「亞伯拉罕誕辰」、「摩西逝世紀念日」這些近乎偶像崇拜的節期。
基督教是活人的宗教,不是死人的宗教(參太八 22 ,「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」)。因為基督徒薄葬不祭祖而說基督徒不孝,顯係無稽之談。聖經要人孝敬,甚至不可藉奉獻上帝之名,忽略對父母的供養(可七11,參提前五8)。可見神要人活時孝順。人一死,子孫再做什麼都沒有用。「樹欲靜而風不止,子欲養而親不待」,這話不也顯示同樣的思想,勸人行孝要及時嗎?生時不孝,死後厚葬祭祀,那是偽善,不會「民德歸厚」。
不僅對父母如此,聖經也要求基督徒珍惜在活人身上的每個作為。馬利亞和約瑟都用香膏膏主。但馬利亞膏活人,所做的是「美事」,普天之下都要記念;約瑟膏死屍,聖經責備他「暗暗的作門徒」(約十九38)。基督徒要專注來生(西三2;林後四18;羅八24),但來生的禍福榮辱,完全決定於今生是否信主愛人。所以,基督教是最實際的宗教,它不因來生廢今生,反倒以今生定來生。今生不信不愛,死後就沒有補救的辦法。生死之界,連亞伯拉罕都不能越過(路十六26)。
基督徒不信人死會變鬼干擾或福佑活人,也不信活人能藉任何儀式活動影響死人。基督教顧蒼生不顧死人。倡導本色神學、搞祭祖掃墓的人,常不肯面對聖經清楚的教訓:死亡終結了人間一切的關係。死後,不論上天堂、下地獄,再沒有今生夫婦以及其他人倫關係(參太二十二23-32)。基督徒以弟兄姊妹或肢體相稱,並不論肉身的輩份。
愛人須及時
我很敬愛的一位高中老師在我留學時死了。回國後,同學知道我和他感情好,就常問:「什麼時候去上老師的墳?」我一直規避,最後對他們說:「你們可以作證,老師生前,我非常關心照顧他。但人死了,任何事對他都不會有影響。我的時間力氣只用在活人上,對你們也一樣。」同學有的以我為怪。但大衛不正是在孩子活的時候切求,死了就沐浴吃喝嗎(撒下十二16-23)?
在美國曾帶著尚襁褓中的孩子參加過一位老師母的喪禮,大家含笑唱凱歌、含淚讚美主。有傷痛,但那是暫時見不到面、如同淚灑機場的傷痛,不是沒有盼望的傷痛(參林後七10;帖前四13)。簡單的喪禮(從死到下葬,不超過四十八小時),送別死人,激勵活人,這不是比為死人勞民傷財好多了?
美國最出色的神學家愛德華滋(Jonathon Edwards)說:「我們易於把親者的死看為災禍臨頭,哀慟他們如今埋在幽暗的墳墓中……這乃是由於我們的軟弱;其實他們是在幸福之境,享受想像不到的福分……他們在世時,縱令百事順利,仍多有拂逆和憂患,但如今諸般困危橫逆都告終結。」(《選集》,p.131)信徒之死,是到樂境;我們當為他們高興。非信徒之死,是萬劫不復;難過也沒用。厚葬是多餘的,薄葬甚至非葬才好。
我把這經驗告訴一位中國大陸留學生,他大吃一驚:「怎麼讓小孩到殯儀館。那很不吉利啊!」我不禁反問:「虧你還是個無神論、唯物主義者。這麼迷信啊!」其實不信主的人,管他無神不無神,都是迷信的。毛澤東(名義上無神論)、蔣介石(名義上基督徒)、許多華人科學家及權貴,也都很「本土」,深信堪輿命相。世俗化的基督徒也有各樣忌諱。世俗化的大學和神學院中,關於送終、安慰將死的和未亡家屬的課程,漸成顯學。
當然,基督徒是勸慰之子,但我們應該用福音安慰勸化活人。接受福音信靠基督的人,不大需要其他的東西來減輕對死亡的憂懼(愈信愈不需要)。不接受的人,再多的慰藉 ,也是枉然。
非基督徒看死亡
現在我們觸及問題核心:如何看死亡?非基督徒對此有兩個看法:一個是提供死後極樂世界,來克服對死亡的害怕;另一個不訴諸宗教。我們要談的是後者。
以彼古羅說,人怕死是因為以為死很痛苦,死後靈魂要受煎熬。他認為這是錯誤的。死毫無痛苦,死後也沒有靈魂。死不可怕,它像無意識的睡眠狀態。
以彼古羅錯了。人怕死並不因為死很痛。人怕死的重要原因,是我們懼怕那種永遠失去意識的狀態。存在主義者Unamuno(烏納穆諾)說:「我從小就不怕描述地獄恐怖的圖書和文章。只有一件事真可怕,就是虛無(按,包括無意識)。」
斯多亞派的Seneca(辛尼加)主張,要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只有一個法子,就是常常思想它。不過要想得對,要提醒自己: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,要安於大自然賦予我們的命運。人生像宴會和舞台一樣。宴會結束了(該死了),客人就當知趣的退席;戲演完了,演員就當優雅的下台。拒退不下(怕死)的人不通情、不達理。
Spinoza (史賓諾沙)則說:「自由人不應思想死亡。他的智慧論生不論死」(Ethics, LXVII)( 有點孔子的「未知生、焉之死」之意)。
達文西和Condorcet(孔多塞,法國數學家與哲學家)、羅素這些理性主義者,綜合Seneca及Spinoza,也談死,不過從生論死。達文西說,人白天活得愉快,晚上睡得也安舒。生死類同醒睡,我們要盡量使自己活得愉快,死就不足懼了。
這話說來簡單,但未免倒果為因。應先除去隨時威脅我們的死亡陰影,今生才真能活得愉快。要人先快樂的活,因而不怕死,那並未解決問題而是不面對現實。面對或思想死亡,有幾個人能像斯多亞派那樣瀟灑的思想死、不怕死呢?
存在主義哲學家和上述學者有異有同。同理性主義一樣,他們鼓勵人思想生,不過要思想生的荒謬;同斯多亞派一樣,他們更要人思想死,不過是思想死帶來的虛空。
維根斯坦在維也納的時候,該地的知識份子和作家Karl Kraus、音樂家Mahler、Schoenberg,前衛派建築師Adolf Loos,都有華格納「諸神的黃昏」之氣質。他們感覺,歐洲文明、歷史要崩潰要結束了;人類除了等待滅亡外,只有一條路好走:「自殺」(梁啟超遊這樣的歐洲,才會寫出《歐遊心影錄》那樣東風壓西風的文章)。
人生的目的是自殺。這不是悲觀主義充斥的維也納才如此。柏拉圖就說過,哲學即學死;叔本華也說,人生如拚命的駛舟前進,經過無數的狂風大浪,克服一切危險後,卻在死之礁石前,全舟粉碎。海德格跟著說,人生以死亡為目的。維根斯坦的三個兄弟,接受當時一位猶太作家Otto Weininger在“Sexand Character”書中的建議,自殺身亡。Weininger自己在貝多芬死去的屋子裡自殺。維根斯坦沒走上此路,不過他激賞Weininger及Spengler(史賓格勒)的《西方的沒落》。他說:「哲學家的光環,消失在這個文化頹喪的時代中。」
自殺的論調,我覺得在中國文化中是罕見的。中國思想中有看破生死的(如莊子),但極少討論及鼓吹自殺的(忠君愛國而死不算自殺)。凡夫俗子更是以長壽為鵠的。也許中國苦難太多,愈苦愈要活下去,不會想「自殺」這種「古怪」的事。
基督教當然反對自殺,說死是咒詛、壞事。不過鼓吹自殺的西方人有一點是對的,就是顯示出:沒有神的人生沒有意義。
延壽而不除罪?
哲學家和宗教家提出面對死的辦法,恐不如科學家的辦法實際。科學家走的是秦始皇的路:找出不死的仙丹。可是這個最實際的辦法,大概也是最不理想的。因科學家(及千千萬萬求長生不老的人,包括許多基督徒)忽略了叫人最痛苦的,是罪不是死。
死不是最壞的事。不但不是,在人類墮落的狀況下,死還有它積極的作用。看幾個例子:希臘神話的黎明女神Aurora(奧羅拉)愛上了英俊的凡人Tithonus(提同諾斯),但凡人會死,Aurora求Zeus(宙斯)賜Tithonus不死。Zeus答應了。Tithonus真的永生不死。可是Aurora忘了求Zeus使Tithonus青春永駐。於是Tithonus逐漸老化,眼瞎耳聾、頭白齒落、面皺身僂、拄杖羸步、喘息而行,然而他不會死。死神不能近他。他得永遠老化下去。最後女神關門,離他而去。
Prom etheus (普羅米修斯)的遭遇是第二個例子。他因盜天火給人類,被處以極刑。極刑不是死刑:比較之下,死刑還好過些;極刑是被縛於石山上,每天有鷹來啄食內臟,但Zeus賦他不死之能,所以儘管天天痛徹心腹,卻不會死。
對這兩位人物而言:死實在不是最壞的;若苦而死不得,那才是最壞的。
第三個例子是王爾德的小說人物Gray(《葛雷的畫像》)。他和魔鬼作了交易,能一直風流倜儻,憑著美貌青春,玩盡女人,傷盡男人。叫人又妒又恨。小說提醒讀者,健美而心惡,可怕極了。
想一想,如果發明不死仙丹,毛澤東和千千萬萬的大小罪人(包括叫你受不了的老闆、同事、婆媳、家人和我們自己)都不會死,繼續犯罪傷害人並被罪惡傷害,那多可怕?地獄不正是這種求死不得,沒有死來解脫痛苦的地方?(參啟九6,「……人要求死,決不得死;願意死,死卻遠避他們。」)。神讓「死」臨在罪惡的世界,固然是審判,但也有縮短痛苦的好處。
死不是最壞的事,復活和永生卻不一定是好事。如果,復活的人一如往昔的自私自利,永生者習以為常的只顧自己,而這個世界又一直充滿了細菌、病毒、天災、人禍。那麼,科學家即使提供延年益壽之道,也將是醜惡和罪孽的延續與擴大,而不是給人真幸福。
耶穌說,人若不重生,就不能進神的國。真的,如果天堂之門大開,人人可進(如某些樂觀的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);那麼,天堂很快會變成地獄。因為自我中心的罪人,會用未曾重生的老我,把邪惡的心思言行,帶到天堂而敗壞天堂。永生不是延年益壽;永生是脫下舊人,穿上新人;用Dorothy L. Sayers(1893-1957 )的話,“ Eternityabolishes time, not prolongstime.”就是「永恆廢掉時間,而不是延長時間」。
死不是最壞的事,因著死亡,許多罪惡和痛苦都停止了。從環保生態來看,不易分解(不會死)如塑膠這類東西最有害。幸好有死亡,許多暴君無法不休止的傷害人。死這個壞東西,也有它的用處。這正是奧古斯丁反駁Manichean二元論所說的話:「再壞的東西,也有好處。」(Nonigiturpotest esse malum, nisi aliquodbonum.)
死的確是可怕的仇敵。但在神全能的掌管下,最可怕的不是死,而是罪:「死的毒鈎就是罪」(林前十五56)。死是犯罪的刑罰,沒有罪就沒有死。不對付罪而想延年益壽,就算成功,也只是延長罪惡的痛苦。神給的永生,不是在罪中不斷的生活,而是永遠活出像神那樣良善的生命。
可惜,世俗化的基督徒愛世界不愛神:死是離開世間,所以他們怕死;罪是離開神,所以他們不怕罪。甚至一聽到死,就如喪考妣,覺得離世(死)見主,壞得無比。凡不專心跟隨信靠主的人,都會因愈老愈怕死。而愈怕死愈無安全感,也就因此愈可怕。
孔子說老而不死是為賊,道盡不認識主恩者的情形。他們明知將因老死失去一切。但心有不甘,又不肯信主保平安,於是戒之在得,又貪得無厭──知道自己不討人喜歡,又鼓吹後人要紀念他(祭祖)。非基督教文明葬禮的浩大,不信主者花時間、精神在死人的身上,都清楚顯示,唯獨神賜生命,而且越發豐盛。神以外的,「 無非要偷竊、殺害、毀壞」(約十10)。
主的門徒會愈老愈可愛,「外體雖然毀壞,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」(林後四16)。我接觸過不少的長輩。他們因信靠主而不自私,和藹可親,體貼晚輩,自己有平安,又把平安分享給人。
有一次,我同上面談到的那位老師母的女兒聊天,我禮貌的問:「妳常去母親的墳上嗎?」她答:「從來沒去過。你是傳道人還不知道,她不在那裡嗎?」中國人很難接受如此「不孝」的思想。但仔細想想,這不正是天使在主復活早晨那「榮耀宣告的迴響」嗎:「祂不在這裡,已經復活了……。」(路二十四6)為什麼我們還在死人中找活人?為了可不可以火葬、喪禮如何才隆重,花力氣時間呢?死不是我們要關心的事,活才是呀!這必朽壞的如何葬有什麼關係?神要幾塊臭骨頭才能叫人復活嗎?小信的人哪!
這位不上墳的姊妹,是兒女中最孝順的一位。母親生時最受她照顧,在這個女兒家過世。她在教會最熱心事奉,最樂意幫助人。這是真實的基督徒,她造福活人,沒有把時間精力浪費在死人身上。 (摘自《基督徒最後的試探》,雅歌出版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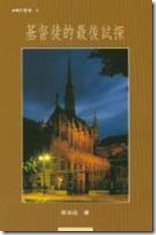 《基督徒的最後試探》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ians,康來昌著,雅歌出版1995.6出版
《基督徒的最後試探》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ians,康來昌著,雅歌出版1995.6出版
本文作者:康來昌牧師
資料來源:台北信友堂2014.4月份《信友通訊》